以案释法 | 房屋委托代管合同中受托人死亡,其继承人是否享有代管权——兼评《民法典》第936条之“采取必要措施”


以案释法 | 房屋委托代管合同中受托人死亡,其继承人是否享有代管权——兼评《民法典》第936条之“采取必要措施”
黄甲和黄乙系兄弟,双方各有农村房屋一间,黄甲妻子为林一,黄乙妻子为陈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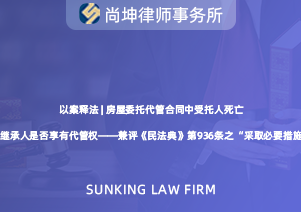

案情简介
黄甲和黄乙系兄弟,双方各有农村房屋一间,黄甲妻子为林一,黄乙妻子为陈丙。在1937年前后,黄甲夫妇和黄乙前往南洋谋生,黄乙妻陈丙留在国内。尔后,黄乙在南洋病逝,黄甲与林一回国向陈丙告知其夫死讯,之后陈丙改嫁同村黄丙。黄甲和林一在离开国内后,其房屋由林一母亲居住,黄乙的房屋由陈丙进行居住。1960年前后,黄丁向林一母亲借住其居住的房屋。林一得知后,写信委托林二代为管理房屋,并要求林二向黄丁要回其所有的房屋。1982年林二向法院起诉要求黄丁返还房屋,在法院的调解下,双方达成黄丁返还房屋给林二代管并支付400元租金的协议,并制作了调解书,但是该调解书至今并未履行。陈丙与黄丙生有一子黄福,黄福生有女儿小黄,黄丁生有儿子黄东。1995年,当地国土部门给黄福、黄东颁发集体用地建设使用权证,明确了各自所有的房屋面积。受托人林二于2009年离世。2020年因为当地地铁建设需要,政府对上述2套房屋进行征收,按照上述土地权属证书的面积数对黄东和小黄(黄福在同个时间将房屋赠与给其女小黄)进行货币补偿和房屋安置。林二生有一子林强,在得知上述情况后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一黄东、被告二黄福、被告三小黄返还征迁补偿款和安置的房屋由其代管,并将当地政府列为了第三人。与此同时,原告林强亦以当地国土自然资源局为被告,黄福与小黄为第三人提起撤销集体用地建设使用权证的行政诉讼【业经两级法院审理,两级法院均认定本案的起诉期限已超过,故均予以驳回】(人物关系:黄甲妻林一,林一弟林二,林二子林强;黄乙妻陈丙,陈丙与黄丙再婚生子黄福,黄福女小黄;黄丁子黄东)

1、原告律师:①原告律师为论证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其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三十四条(委托人死亡、终止或者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终止的,委托合同终止;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根据委托事务的性质不宜终止的除外。)与第九百三十六条(因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被宣告破产、解散,致使委托合同终止的,受托人的继承人、遗产管理人、法定代理人或者清算人应当及时通知委托人。因委托合同终止将损害委托人利益的,在委托人作出善后处理之前,受托人的继承人、遗产管理人、法定代理人或者清算人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原告律师认为,本案系侵害海外华侨利益,因长期联系不上黄甲与林一的后人,依照该房屋代管委托合同性质,该合同不宜终止,原告为受托人的继承人,可以继承该合同权利义务,仍然享有代管权。依据《民法典》936条“必要措施”之规定,该必要措施就包含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原告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是适格的当事人。②原告引述1981年《民事调解书》的内容,以证明黄丁无权占有黄甲房屋的事实,因此黄东亦为无权占有人,原告基于委托合同请求黄东返还其获得的土地补偿款及安置房屋由原告代管。③原告认为,黄乙的房屋应由黄甲继承,因此该房屋也应由原告代管,被告二与被告三所获得的物上代位物亦应由其代管,被告二与被告三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被告一律师:①原告不是本案适格当事人,无权提起本案诉讼。原告不是委托代管合同一方当事人,亦不是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房屋代管权不属于遗产,依法不得继承。②拆迁补偿安置费包含二次装修补偿费、附属物补偿费及其他奖励等费用,均为拆迁部门用于补偿安置房屋实际居住人,与房屋产权无关,原告要求拆迁补偿款归其代管的诉求不能成立。③讼争房屋所有人记载为黄甲,林一虽系黄甲的妻子,但未必就是产权人或唯一产权人,林一是否有权对房屋进行处分,明显缺乏证据予以证实。④调解书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调解书制作后是否经过送达无法证实,且该调解书已超过申请执行期限。⑤十几年前黄甲之孙由印尼回家祭祖,期间有向其说明房屋情况,黄甲之孙表示不收回房屋,并表示由黄丁及后人居住,要求黄丁每年其祖先忌日进行祭拜。
3、被告二与被告三律师:本案我们是被告二与被告三的代理人。本案胜诉的关键在于:首先,论证原告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一旦法院认为主体不适格或者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具有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础权利,那么就会产生裁定驳回起诉或者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法律效果;其次,本案的案由虽然是拆迁补偿合同纠纷,但是本案中夹杂着一层继承法律关系(即原告认为黄乙房屋由黄甲继承,因此基于继承关系,原告亦有权予以代管黄乙的房屋)。但是我们认为,此系原告律师理解法律错误,因此需要对此予以反驳。一旦得出黄甲并非黄乙房屋的继承人,那么原告就无权向被告二与被告三提起诉讼;再者,原告提供的调解书仅载明由黄丁归还一间房屋由林二代管,并没有涉及到被告二与被告三讼争的房屋,原告亦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对被告二与被告三讼争房屋具有代管权;最后,被告二与被告三获得拆迁补偿款和房屋安置的依据是当地国土局颁发给被告二的集体用地建设使用权证,其性质上属于物权权属证书。在两级法院均对原告提起的行政诉讼作出否定性评价后,该物权权属证书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因此即便法院最后认定委托合同没有终止,亦不会影响到法院对被告二与被告三讼争房屋的处理结果。
基于上述思考,我们提出如下答辩意见:①林强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其无权提起本案诉讼。根据民法理论及《民法典》九百三十四条之规定,房屋代管行为系委托行为。委托合同是以双方信任作为基础,属于人格专属性的法律关系。一旦委托人或受托人一方死亡,委托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对死亡一方的人身信任的物质基础就不复存在,此时委托合同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终止。本案中,即使认为林一与林二之间成立房屋代管委托合同关系,但在林二死亡后,二者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就应该终止,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此消灭,且不得继承。代管权具有极强的人身专属性,即便原告作为林二的继承人也无权继承该权利。因此,由于原告在实体法上不享有本权,故不享有诉之利益,因此原告不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无权提起本案诉讼。(关于原告主张该委托合同依性质不宜终止及采取诉讼的必要措施,后文会提及)②答辩人黄福系讼争房屋的合法继承人,原告无权予以代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条、一千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配偶、子女、父母是第一顺序维承人。夫妻一方死亡后,生存的另一方作为死者的配偶依法属于死者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依照法律的直接规定继承该遗产份额。在遗产分割完毕后,生存的配偶便享有了对所分得遗产的所有权,有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这部分财产。生存的配偶如果再婚,当然有权对其取得的遗产进行处分,既可以把该项财产带到再婚家庭中使用,也可赠送他人或作其他处理。因此,陈丙在黄乙死后改嫁,但是其仍然是讼争房屋合法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作为陈丙的儿子黄福,在陈丙死后当然享有继承权并拥有对讼争房屋的处分权。因此,原告在起诉状认为黄乙房屋由黄甲继承,不符合事实,亦违反法律的有关规定。③《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系国土部门依法定程序审批、核准给答辩人黄福,该行政确认行为合法有效。答辩人小黄与人民政府签订《集体土地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从而获得征迁补偿款与房屋安置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理由不赘述)。④原告提供的调解书,其内容无法证明其对黄乙房屋具有代管权(理由不赘述)。⑤答辩人黄福亦非本案适格的被告。首先,在本案中,黄福已将上述讼争房屋及其附着的土地使用权赠与其女小黄,因此其与本案不存在利害关系,本案的审理结果不会影响其权利义务;其次,原告在诉讼请求中要求被告二与被告三承担连带责任,可是黄福如今不是讼争房屋的所有权人,亦不是土地使用权人,相关法律更无连带责任的有关规定。因此原告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最后,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是小黄,并非是黄福。本案为拆迁补偿合同纠纷,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黄福并非合同当事人,因此原告将黄福列为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4、第三人律师:作为拆迁补偿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法院审理结果也许会产生变更拆迁补偿合同相对方的法律效果。但实质上对于第三人来说,不管本案审理结果如何,拆迁补偿款都要向权利人发放,因此本案第三人只需要求法院依法裁判即可。但是第三人律师也提出2点答辩意见。其一,第三人律师认为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仍然享有代管权;其二,客观阐述了政府部门征迁补偿的过程,证明第三人征迁补偿过程合法,对于被告一、三的征迁补偿和房屋安置皆有法律与事实依据。
一审法院【案号:(2022)闽0681民初1880号】: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诉讼时效是否超过问题;二、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以及代管诉求是否成立问题。对此,本院予以分析、认定如下:一、关于本案诉讼时效是否超过问题。本院认为,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分别发生于2020年、2021年,原告以案涉房屋代管人身份于2022年4月2日提起诉讼,本案诉讼时效尚未超过。二、关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以及代管诉求是否成立问题。原告主张其对黄甲、黄乙址在XXXXX房屋各一间享有委托代管权,并提供以下证据:2021年3月29日XX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户口注销证明》,《声明书》,《调解书》、编号xxx的《集体土地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编号xxx的《集体土地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土地使用权申请登记具结书》(黄东)、土地登记审批表。被告及第三人均对原告的证明主张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调解书》认定林二对林一址在XXXXX房屋一间享有代管权,双方之间存在房屋代管关系。现林一、林二均已亡故多年,原告也未能提供相关代管委托手续,其以林二继承人身份主张对《调解书》项下房屋享有代管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另原告主张其对黄乙址在XXXX房屋一间享有代管权,亦缺乏证据证实,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原告举证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林强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案号:(2022)闽06民终2422号】: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并未认定林强无诉讼主体资格,只是认为其以林二继承人身份主张对案涉房屋享有代管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故林强上诉主张一审应裁定驳回起诉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据《调解书》确认,林二对林一址在XXXX房屋一间享有代管权,双方之间存在房屋代管关系。现林一、林二均已亡故多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三十四条规定:委托人死亡、终止或者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终止的,委托合同终止;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根据委托事务的性质不宜终止的除外。故林强主张以林二继承人身份对案涉房屋享有代管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同理,林强上诉主张对黄乙的房屋行使代管权的理由亦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至于上诉人主张黄东因侵占取得房屋所有权属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作审查。综上,林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从一审法院的裁判上看,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合同因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死亡而终止,在没有证据证明委托人或者委托人后人对原告进行重新授权时,一审法院否认了原告享有代管权。在某种程度上说,一审法院亦否认本案房屋代管合同的性质属于民法典934条中规定合同不宜终止的例外情形。在主体资格上,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是适格当事人,但是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为委托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故一审法院以判决的形式驳回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亦认为林强不是案涉委托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案涉合同已经因林一与林二的过世而终止,从侧面反映了二审法院亦不认可本案房屋代管合同的性质属于民法典934条中规定合同不宜终止的例外情形。
关于本案房屋代管合同的性质是否属于民法典934条中规定合同不宜终止的例外情形属于价值判断问题,一二审法院均没有对此进行详细说理。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因委托事务的性质不宜终止的,存在于一些特殊的委托合同中。例如,甲委托乙企业生产医疗物资,用于某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情况十分紧急。如果此时委托人甲因感染新冠肺炎不幸逝世,由于委托事务是生产抗击疫情急需的医疗物资,性质十分特殊,在这种情况下,这批医疗物资不能停止生产,委托合同不能因委托人甲的死亡而终止。而在本案中,首先,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均有物权权属证书,而且在另案行政诉讼中未被法院撤销的情况下,一、二审法院一旦作出肯定性评价,将会使案涉房屋权属陷入不确定状态,不利于社会安定;其次,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委托合同不宜终止的情形非常少,除非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否则法院一般不予认定委托合同存在不宜终止的情形,其理论的逻辑起点在于委托合同具有一定的人身专属性,信任基础是合同存续的关键所在,因此需要对委托合同不宜终止的情形进行严格限制;最后,即便法院认定该案涉委托合同属于不宜终止的情形,根据物权优于债权的民法理论,在合法有效的物权权属证书面前,原告依然免不了败诉的结果。
虽然本案的胜诉在意料之中,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原告律师所做的努力。原告律师援引《民法典》934条极力论证本案委托合同属于不宜终止的情形,以期以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身份参与诉讼。又援引《民法典》936条中的“必要措施”作为其提起诉讼的依据,虽然一、二审对此并没有回应,但笔者认为原告律师援引该条作为本案的请求权基础并不恰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三十六条
因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被宣告破产、解散,致使委托合同终止的,受托人的继承人、遗产管理人、法定代理人或者清算人应当及时通知委托人。因委托合同终止将损害委托人利益的,在委托人作出善后处理之前,受托人的继承人、遗产管理人、法定代理人或者清算人应当采取必要措施。
此处所谓“必要措施”,是指受托人的继承人、法定代理人或者清算组织为防止委托人利益受损采取的合乎委托合同目的的相应措施。此必要措施应作广义解释,既包括消极的保存行为,如保管好委托事务有关的票据单证和资料及委托事务的财产等;也包括积极的对委托事务的处理行为,如委托理财中,基于对市场风险等专业判断及时采取止损措施等。
由于采取必要措施义务在性质上属于后合同义务,而且其义务主体是受托人的继承人、遗产管理人、法定代理人或清算人,也即其义务主体并非委托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法定的义务已经超越了合同相对性,故对于这种义务,除非当事人有特别约定,法律应当考虑设置该种义务的必要性、适当性、合理性等因素。基于此,本条也对采取必要措施义务进行了限制:一是目的性限制,即采取必要措施必须是出于防止委托人利益受损,唯有如此,采取必要措施才有正当性和合目的性,否则,便无必要采取措施;二是必要性限制,即采取措施不但要出于保护委托人利益之目的,而且该种措施也是必要的,而非过度的和非必要的:三是时间限制,委托人的继承人等主体介人委托事务的时间起于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终止事由出现之时,止于委托人作出善后处理之时。但是,对此条的理解,也不应太过于机械,如受托人已处于弥留昏迷之际,如不对委托事务采取必要措施,委托人利益将遭受巨大损失,此时受托人的继承人为保护委托人利益受损,果断采取措施,也可参照为本条规定处理。
本条规定的“采取必要措施”与本法第935条规定的“继续处理委托事务”不同,即只是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减少委托人因委托合同终止产生的损失,而实际上委托已经终止,受托人的继承人等没有义务继续处理委托事务。法律规定受托人的继承人、遗产管理人、法定代理人或者清算人承担上述通知义务和采取必要措施的义务,是因为受托人死亡后,继承人有继承其财产的权利,在遗产分割前由遗产管理人接管相关财产、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受托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由法定代理人代理其民事活动;法人被宣告破产或者解散后,由清算人接管,对财产清理、保管、估价、处理和分配,清算人可以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继承人、遗产管理人、法定代理人、清算人,在承受受托人遗产或者处理受托人事务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将受托人的有关事宜妥善处理。
回归本案,基于上述思考,笔者认为原告以该条规定“必要措施”作为其提起诉讼的依据并不恰当。上述法律规定并没有赋予受托人的继承人提起诉讼的权利与依据,原告作为受托人的继承人在履行采取必要措施义务时权限不包括行使代管权。在原告没有合同权利——代管权时,其无权提起诉讼要求被告一与被告三所获得的补偿款和房屋安置进行代管。在笔者看来,原告应在委托代管合同终止后,积极履行通知委托人的义务,由委托人或委托人的继承人作为适格主体提起有关诉讼,而不是原告怠于履行通知义务,却以自身名义提起本案诉讼以期达到变相确权的目的,此行为与民法公平、诚实信用原则相违背。
委托合同是以双方信任作为基础,属于人格专属性的法律关系。一旦委托人或受托人一方死亡,委托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对死亡一方的人身信任的物质基础就不复存在,因此委托合同原则上应终止,除非有当事人约定或者其他不宜终止情形。因此,委托合同任何一方当事人的继承人原则上均无法履行该合同的权利义务。委托合同中不宜终止的情形在实践中凤毛麟角,法院对此依然保持谨慎的态度。《民法典》936条之“必要措施”产生于合同履行完毕之后,其义务内容不包括合同本身的义务,因此委托合同受托人的继承人仅在某些特定情形下需要履行该后合同义务。而本案中,原告援引该条作为请求权基础并不恰当。